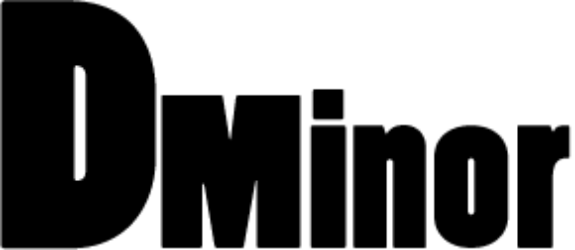0308021235 MEW
流暢甜美的噪音傳來,我們一行人開始從Indoor Stage的入口向會場加速奔馳。那樣的音樂十分適合用來奔跑,很直覺的便可以聯想到三兩成群在街頭跳躍前行的年輕男女,陽光灑落,西裝比挺的中年上班族在一旁側目,世界尋常平淡地運行,只有我們充滿希望地朝反方向前去…
這是我對MEW的第一印象,充滿北方冰冷靈氣的Dream/Noise Pop,然而在酥麻擴張的吉他聲響包裹下,卻又顯得異常溫暖調和。我穿越過人群,心情因興奮而鼓動著,聲音越來越近,我的身體也彷若被張開雙手迎接的光線擁抱而變得舒坦,像是鮪魚肚肉的脂肪在我的聽覺裡溶化擴散。強烈的鼓擊催促著我的腳步,也許在這一瞬間身體反射性地感覺需要這樣的刺激,它已經癱瘓在低調冰涼的氣氛裡太久。
會來看MEW是因為朋友在行前的付託,因為同一個時段在Outdoor Stage是Tokyo Ska Paradise Ochestra,但說實在的,這才是屬於我的調性。乾淨帶有童稚的高音,沒有一絲華麗樂團所配備的陰柔邪氣─雖然那是我的最愛─而是屬於北國灌木叢林的冰雪氣質。曲勢和絃已是近乎於八零年代流行曲般流暢,若是單純抽離旋律的部分,幾乎首首都可以成為朗朗上口的通俗暢銷曲。但是某些歌曲的吉他和節奏部分卻又極端矛盾的破裂和攝人,接近Post-Grunge式的激烈作風。而當主唱Jonas飄邈呢喃地吟唱時,感覺卻又流向了新迷幻的氣味…
我們在這樣一個充滿新舊衝突的新興樂團面前,像是回到青春時代尋找回憶似的悵然,又像迎接未知生命的少年般充滿光亮。我眼前展開許久未有的寬闊,將我吞入徹底明亮的白色強光裡。
0308021445 GO!GO!7188
午餐只吃了一份日式炒麵和麒麟啤酒果腹,在吸煙區抽了三支機場買的萬寶路淡煙。外面的天氣還是熱得像是一切都要被溶化一般,我們選擇留在室內的Sonic Stage。方才領教了一會兒外頭的炙熱艷陽,開始覺得吹著冷氣看表演是莫大的幸福。
舞台上仍在準備,我的神智因為過於舒適而漂離,想起在了入口處發塑膠袋的女孩們,烈日當頭,臉上依然堆滿笑容,嘴巴裡親切有禮地念著我聽不懂的日語,聲音都是甜甜扁扁的,很有一致性,至少是一致地符合我膚淺印象裡的日本女孩典型—白晰、甜美、有禮、順從、小女人…
腦袋裡一邊想著,另一邊聽著朋友敬一桑在我耳邊對GO!GO!7188做的簡單敘述。我不是十分專心地聽著,大概是說:龐克、兩女一男三人團、在日本頗有名氣、兩個女孩覺得自己是有著女兒身的男人…等等。我心裡暗想,很多女孩子都喜歡這麼說,雖然我不明白這些人為什麼喜歡自認為—或是希望別人認為—他們是男人,但我其實都有些不以為然。女人就是女人,雖然說我對女性沒有任何輕蔑的意思…
台下響起了歡呼聲,我停止思考那些無聊的問題,兩個纖瘦留著長髮的可愛女孩已經站在台上,他們身上的吉他和貝斯,比例上因為有些過於巨大而顯得不協調。服裝上沒有誇張的打扮,身上也沒有怪異的裝飾,但是一眼就可以知道他們是搖滾女孩,有那樣的氣質。貝斯手浜田亜紀子咧著她的大嘴微笑,感覺隨性的說了幾句話,似乎有些挑釁煽動的意味,接著,1-2-3-4…
我傻了。
所驚愕的不是全場瘋狂的跳躍鼓譟,不是音樂急速衝刺的兇狠威猛,也不是吉他音箱低沈粗重的號叫。是氣勢!是兩個可愛的女孩子在我面前展露的骸人氣勢,讓我不由自主的感到無比亢奮,肢體隨著鼓點開始搖擺—上下、左右、前後,直到雙腳騰空。扭曲近乎撕裂的吉他和貝斯震波,在眼前形成兩隻龐然巨獸,搭配上日式演歌的古老曲調,以及極其尖銳的女音嘶喊,彷彿浮現了酷斯拉和摩斯拉對決的怪異場景。我在心裡有了結論:她們不是有著女兒身的男人,而是比許多男人恐怖無數倍的某種生物,身為男人的我,被她們拿來相提並論,都感到自慚形愧…
整場表演在幾乎沒有停止的狀態下帶領我們全速狂奔,結束後身體還有一絲絲高速行駛下的無重力感。隨著人群拖著蹣跚的腳步離開會場,我們到有大面落地玻璃的吸煙區坐下,一時間還無法跳開剛剛那個詭異的畫面。我大口地啜飲海尼根生啤,思索著發塑膠袋的女孩,GO!GO!7188,還有這個充滿強烈衝突矛盾的國家。想了一會兒,也就累了,我決定放棄,回到現實,繼續享受這約莫只有半小時的悠閒…
0308021945 BLUR
之後我們又去看了Starsailor和Jon Spencer Blues Explosion。簡單的說,Starsailor等於一個很大的呵欠(我們六人參訪團一致贊成此說法)。J.S.B.X.的現場力道剛開始令人驚豔,尤其主唱Jon Spencer金凱瑞式的歇斯底里唱腔魅力十足,但由於歌曲的旋律線原本就不明顯,加上沒有低音吉他帶領,到中後段難免令人生膩。
說實話,其實今天一整天的等待就是為了Blur,我站在舞台前中央約二十多排左右,可以很清楚看見Damon Albarn的絕佳位置。
對於Blur一直有著十分複雜的情感,他是我十七歲陷入Britpop狂熱期便開始聽到現在的樂團,卻也是在那股風潮中唯一不曾迷戀的一支樂團。甚至有一段時間我對”The Great Escape”有著莫名的極端厭惡,諷刺的是,這次唯一讓我感到心頭震動的一首歌,卻是在其中的”Universal”。
我想一切都是因為回憶在腦中產生的化學作用。其餘的部分,只是感覺十分的不真實,前一晚極度的睡眠缺乏,站了一整天的疲累,加上擁擠人群裡的悶熱和旁邊觀眾手臂上黏漬的汗水;Damon Albarn穿著會讓人誤認為George Michael的裝扮,站在距離我只有約一百公尺的地方,彈奏吉他的卻不是Graham Coxon熟悉的身影,兩旁巨大喇叭播送的是和專輯幾乎沒有差別的完整音色;而當”Crazy Beat”和”Song 2”這兩首歌連續演唱的情況下,四周人群接近失去理智的瘋狂衝撞,讓我幾乎沒有辦法對當時的表演留下任何印象;閃動的燈光,三位黑人合音千古不變的搖曳之姿,兩套鼓組奮力地埋頭敲擊,Alex James一貫瀏海半掩著播弄Double Bass的神情,Damon Albarn明顯蒼老的臉龐,興奮、感動、回憶、激昂、躁熱、憂傷、疲憊、錯亂…這一切在我腦中快速旋轉,揉捏成一團五顏六色並且錯雜繽紛的塊狀物體,帶著些許夢境和虛幻的在我腦中的某個部位盤據;然而,Blur依舊無法帶給我隔天在聽Stereophonics唱”Local Boy in the Photograph”時那樣的情緒滿溢,或是聽Radiohead時被徹底震撼所感覺的靈魂潰散瓦解。除了在”Universal”的某一瞬間,我回到了過去—十八歲時的青澀光景,在那一剎那,以快速到無法清楚感知的速度在腦中湧現,
於是,我放任自己恍惚的意識,隨著陪我長大的Damon Albarn,哼唱著,屬於我自己的青春…
那是當晚我心中最美的一刻。
0308031945 RADIOHEAD
Radiohead的現場震撼足以讓人靈魂潰散。 當晚海洋球場觀眾爆滿,人數至少比前晚Blur演唱時多出一倍。而一開場的”There There”,三套鼓組的轟隆聲響,加上朦朧煙幕中快速閃動的霓虹燈牆,所爆發出的驚人能量讓之前的樂團都顯得只不過是Radiohead開場前的餘興節目。我站在舞台正前方約二十排左右的位置,人群在興奮中不停騷動著,像是波浪般傾倒搖擺,幾乎失去控制。這場表演他們幾乎包辦了從The Bends到Hail To The Thief的所有經典曲目,唱完第二首安可”Karma Police”之後,Thom Yorke很為難的對台下仍然躁動的觀眾表示:不能再唱了,今天的表演到此結束,接著連續對觀眾行了好幾個日本式九十度鞠躬。大夥想想其實也該過癮了,正逐漸開始停止鼓譟時 ,台上五個人連預備拍都沒有下,冷不防地開始演奏起”Creep”,全場觀眾傻眼了半秒鐘後立刻陷入瘋狂,整個球場追隨著Thom Yorke的歌聲唱和著,天空中散落起活動結束的美麗煙花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