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是我大學的學長,也是我那個夏天的室友。他的身材粗壯,皮膚黝黑,留著一頭篷亂的長髮,和沒有修剪的鬍子。他是一個熱愛爵士樂的背斯手,崇拜Jimi Hendrix的吉他手,但有時也是個把Nine Inch Nails的唱片當作搖籃曲的瘋子。他的裝扮永遠都是一件將汗衫袖子剪掉的白色背心,長袖的格子襯衫,似乎從沒換過的破爛牛仔褲,加上一雙尖頭的咖啡色馬靴;兇惡的臉上帶了一副十分斯文的細框眼鏡。我從他身上,得到了許多關於音樂、電影、文學以及哲學的知識,也學到了賭博、划拳,和上酒店的學問。他曾說,自己一生最大的夢想是在深山裡獨居,過著耕讀式的隱士生活。平時寫小說和劇本,若有性的需求便下山花錢排解。這些話我一直深深地記在心裡,它勾勒了一個藝術家所嚮往的美好世界;但也在日後,成為了深刻呈現現實壓力下人的無力與退讓的殘酷例證…。
我和查理布朗女孩的樂團,一直都停留在玩票性質。練團的次數不多,表演也都是一些校內的活動,曾經有創作過一首歌曲,最後也是不了了之。梅的朋友當時介紹了一個在酒吧裡駐唱的機會,對於在新竹的我們,能夠在外面定期演出是所有樂團夢寐以求的事情。
「你是我遇過最好的主唱,什麼歌都能唱,音域也夠寬,而且表演時十分投入。」
「如果是你來的話一定沒問題。」梅在家裡拍著我的肩膀說。
當天晚上,我和梅,以及另一個寄宿在我們家的學長,開始計畫著組團的事宜。那位寄宿的學長也是一個戲劇性的人物,我剛認識他時,他是一個住在教會弟兄之家的虔誠基督徒,每次看到他都是匆匆一瞥;唯一的印象是一輛很炫的NSR機車,還有黑色的Kramer吉他。他有一張圓圓的臉,稀疏的頭髮平平地鋪在頭頂上,活脫脫就是一隻趾高氣昂的海豹;他的樂團專門玩Led Zeppelin和Ozzy Osburne等七零年代左右的老搖滾,是我們這些學弟妹眼裡十分仰慕的大人物。海豹男孩很少講話,認識他的第一年,幾乎沒聽他說過幾句話。直到大二時的某一天,他忽然主動開口要參加我們的聚會,這時候,大家才發現原來他有很嚴重的大舌頭…。從那天開始,他就變了一個人。他把頭髮留長,自己在屈臣式買了染髮劑把頭髮染成淺褐色。教會的房間也不回去住了,他在社團的角落裡弄了一張草蓆,每天就睡在菸蒂、灰塵、昆蟲,和窗口飄進來落葉堆裡,菸酒、麻將、撞球成了他的代名詞。他是我見過最頹廢的男人,也因為如此,有很長一段時間,他都沒有得到半個女孩子的青睞。
我們計畫要找的另外兩個人,之前都和海豹組過團。鼓手是我上一屆的學長,也是我加入社團時的社長。他有一張稚氣未脫的無邪臉孔,但據說是全社團最早便脫離在室的男人。吉他手比我小一屆,是個純樸的雲林小孩。白淨的皮膚和纖瘦的臉型,尖尖長長的鼻子,加上那雙上揚的桃花眼,很像一隻憨厚老實的狐狸。我和海豹都認為他是一個很有天份的人才,他彈吉他的手法很細膩,而且有著絕佳的音感,大一時只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就抓完了“Goodbye To Romance”的吉他。一切都如預期,他們兩個人一口答應,於是我們便很快地展開密集練習。我和海豹挑了一些自己喜歡的歌曲,大多是90年代後期的Brit-pop、Alternative Rock和70年代左右的Psychedelic Rock。每天下午,我結束在新竹少年監獄的吉他教學後,便來到悶熱的練團室裡排練。在那個永遠只有我們四個人的小房間裡,我揮舞著紅色的SG吉他,用幾近瘋狂的姿態詮釋著心中的經典樂曲。我站在這個充滿著複雜情緒的交叉點上,前所未有的快樂和初次體驗的濃烈苦澀在此刻荒謬地凝聚著。眼前的光線依然渾沌不明,但我似乎就這樣被默默地牽引著,走向了一條再也不會回頭的路。也許在當時我們都從未想過,因為梅那句單純不過的鼓舞,許多人的年輕歲月就因此而改變了。我們的一生中存在著太多的意外,那些被遺忘的或是不經意的話語,卻常常足以徹底地扭轉命運的軌跡。三年前,梅和一個認識不到兩週的女孩子閃電結婚。他不再說著到山中隱居的夢想,而是很務實地在科學園區擔任業務方面的工作。也許對他來說,那些耕讀生活的嚮往不過是少年時青澀的豪語;但對我而言,卻永遠是佇立在心中的巨大標的。自從他的婚禮之後,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,在我自己所設定的時間與角色裡,他依然是那個穿著破爛衣服,手裡拿著白長壽和伏特加,嘴裡談著音樂與哲學的青年藝術家。時間消磨了很多年少的幻想,我不知道是什麼讓他改變,也許是所謂的性格,也許,是某個人不經意的一句話。但我知道,因為他,我支撐起自己午夜夢迴的聲音;成為了自己希望成為的人。
駐唱的過程並沒有想像中的順利。朋友介紹的那間酒吧,我們只去過兩次。第一次表演時,台下只有兩桌的聽眾,一桌是梅和其他幾個朋友;另一桌是一位留著平頭、穿著短袖水洗絲襯衫,懷裡還摟著一個女人的道上兄弟。我們唱了John Lennon的“Imagine”、Led Zeppelin的“You Shock Me” 、Counting Crowes的“Mr. Jones” 、Suede的“Lazy”,和Oasis的“Stay Young”…等歌曲。整個晚上兩層樓的酒吧裡都是空蕩蕩的,掌聲也是稀稀落落。後來陸續有一些新的酒客入場,不過想當然沒有人是為了聽歌而來;我們拿了生平第一筆表演換得的酬勞,心中卻有些無力,不過依然買了啤酒回社團慶祝。第二次到酒吧準備演出,店經理過來跟我們說,因為入不敷出,他們臨時決定取消樂團表演。不久後,那間店意料中的關門大吉。對於當時已經練習了二三十首歌的我們來說,實在很難接受這個事實。於是我們轉戰另一間酒吧,希望能夠讓這個樂團有繼續存在的意義。第二間店有別於之前,是當時新竹的老外們熱愛聚集的地方;它的位置在新竹市中心的一條狹小巷道內,每到深夜,便會有穿著俗艷的中年女子在巷子裡拉客。如同一般的美式酒吧,骯髒破舊的門口總是會懸掛著百威和海尼根的霓虹燈。昏暗的燈光裡,大家排隊射飛鏢,或是在那張已經被磨平的撞球桌上比劃著八號球。我們在吧台旁的一小塊空間裡,用幾乎不堪使用的音響設備和一套積滿灰塵的爵士鼓開始試唱,印象中表演的是Nirvana的“Smells Like Teen Spirit”和陪伴我渡過許多昏沈午後的“Friday I’m In Love”。店裡的人很滿意我們的演出,特別是一個染了金色頭髮的女服務生,她說她很喜歡Blur。他們希望樂團下個禮拜開始表演,時間是之後的每週二晚上。
興奮的心情沒有持續太久,幾天之後,娃娃臉鼓手因為開學後要開始準備研究所考試,表示要退出樂團。我們尊重他的決定,並且推掉了剛接到的駐唱機會。開學後的迎新發表會,是這個草創組合的最後一場演出。那天晚上,我初次看到了觀眾眼中傾慕的眼神。
幾天後,查理布朗女孩結束美國之行回到了學校。這是我們的第二個樂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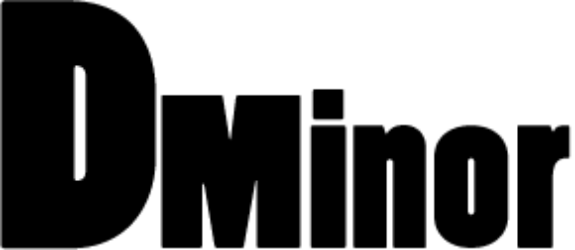
8 Comments on “It’s Friday; I’m in Love(下)”
很多時候….
現實很殘忍的讓你不得不如此….
自己也漸漸的淡忘了最初的感動….
真….被某部份的虛華取代…..
無奈卻也無力是從…..
我想,像我的學長梅,也許也對目前簡單的幸福甘之如飴吧
我們面對的就是不斷的選擇而已
無奈留給那些沒有勇氣的人
只要是面對自己的渴望,不論是單純平實還是轟轟烈烈
都是值得尊敬的
享受生活中簡單的愛,真的是件幸福不過的事了….
但有時也想不顧一切的愛一場
是如此的令人激動!!
有時選擇權不在自己手上時,就放縱自己去享受過程的一切吧!!
老天自有他的安排….
至少現在的我是如此相信!!
很像一隻憨厚老實的狐狸–> haha…有像…
對不起 我離題了:P
以前冠文的狐狸照不知道還在不在
我等一下來找找看
哈哈 是啥狐狸照??
快找找 放來看~~~
狐狸照….
那張應該比較像蚊子吧???
XD 像狐狸可以想像,像蚊子很玄妙…